本帖最后由 文清 于 2015-5-12 17:25 编辑
一觉十年梦,还有谁记得舞文弄墨的文清
中国近代革命与中国传统精神
远古春秋的时光涣漫流淌,好像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运潜移,远看好像静止。而近代社会风云际会,人物辈出。二十世纪初,围绕到底是革命还是改良进行了一番争论。陈天华说:“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梁启超说:“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若强以革命鼓“民气”,势必引起骚乱。最终改良派失败,可若历史不是这个结局,或许会出现另一番景象。梁启超的论断有些道理,为了中国的富强,必经开民智;而开民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恐怕不是革命能开启的。 革命,浅层次说是杀掉异己,深层次是意欲割断历史传统。中国近代百年的革命或是要求西化,或是无所依傍,打破一切现有,从头建造。现在来审视“五四”时期的极端言论,很值得深思。鲁迅都说“中国的汉字都应绑了去杀头”。 中国人的性格很矛盾:表面上可以屈从于任何强势,骨子里却瞧不起任何人,觉得“老子天下第一”;在正经事上没有观点,在非正经事上爱瞎起哄;中国人最难接受革新,但最易丢弃传统。近代不少人士盲从于西方,不切实际的要求全盘西化。例如取消科举制度,而西方民主选举,急切间未能学到,于是政治失去重心。近代中国的革命,偏重在打倒和推翻,不在制度上的改革和建立。社会政治逐步丧失,政治遂一无凭借。革命越彻底,建设就越难。 古代文化有不合理的地方。道德心术越高,或许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让道义和人性共存,那么,他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性格,他可能关键时刻毁灭自己和家人。比如吴起杀妻求将,易牙杀子做菜,金日癉杀长子谢罪,都是心术战胜人性的例子。仁义道德发展到极致就是人性的毁灭,而且叫你不知不觉地觉得这种毁灭是合理的。看来仁义道德的力量真可畏惧,也恰好说明传统文化的力量更可畏惧。 传统精神有许多精华。非是“好古”,非是回护古人,而是古人有颇多可取之处。中国政治制度实在有许多精明独到之处,这是中国式的智慧,西洋人未必学得到。为什么衰乱之世的政治黑暗,因为原先定下的好的制度,渐渐因人事的懈怠而荒废。一般认为,中国古代之学术,惟有史学最发达。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和典籍非常看重。历代社会动乱和改朝换代之际,大量的典籍会被毫不吝惜地销毁。还有,国民对于历史的认识,极其浮浅,及其盲从。他们认为五千年的历史全是封建和黑暗。 “五四”时期对内的口号是打倒“封建”,中国古代史是不是“封建”本质还有待于商榷。父子之间的一片恩情也算封建,连修齐治平的大理想也要打倒,这样漫无目的地打倒,志在扑灭本国民族代代相传之薪火。把传统文化连根拔起,一切人道人文统统不要,全求打倒,这不是向社会盲动势力的革命,而是向中国传统精神的挑战。中国文化至高至深的意义,像《易经》说的“可大可久”,何必步人之后尘。 国家无论盛衰治乱,其已往之历史,在冥冥中必有无限力量,诱导着它未来的方向,不至使其发展轨迹“旁逸斜出”。中国社会的渊源是唐宋以下的形态,其病痛在于无组织,无力量,散漫平铺。它始终维系不散,靠的就是长久的文化传统和强固的民族意识。我们这个民族能延续至今全赖传统文化的保全。传统文化在今仍在渐渐流逝,幸好这棵古树根深蒂固,否则早有断根的一天。要谋求中华之复苏,应着眼于传统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修复上,应寄托于知识分子这个中坚。
杜甫有云“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人之生存,实属大不易。贵重生命,是基本的行事准则。古之杨朱认为如果拔一根腿上的汗毛可以对天下有利,他也不愿意。这虽然极端利己,但至少把个体生命看得很重。中国人的上智在于中庸,什么是中庸,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要做绝了,留点儿回旋的余地,对人对己都是这个道理。什么事情非要用流血来解决呢。天下本一家,像陶渊明说的“落地即兄弟,何必骨肉亲”。《中庸》也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莫不尊亲。” 中国近现代的某些政治运动,好别有用心地发动具有盲目热情的大众来进行捣毁,是对生命的践踏,是对传统人文思想的背离。“隳突乎南北,叫嚣乎东西”,一阵血雨腥风之后,剩下些断壁残垣等待收拾。 历史之所以能前进,就是因为有哪些出头者,商鞅,晁错,贾谊,……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恐怕还要洒更多的鲜血。中国这个社会,自古,挪动一条板凳都不知要流多少血。因此,改良尚须慎重,何况施用不得已而为之的武力。 革故鼎新的殷血已经流淌了数十年,凭借武力的胜败,是最惨痛的教训。须知“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要牺牲生命,是中下策。“止戈为武”,“武”不是武力和暴力,而是追求和平的境界。历史上大凡谥号为“武”的皇帝,都不是好杀伐的“独夫”,而是能威服四海的君主。这个“武”是“武功”,而不是“武力”,旨在求国土安宁。我们的民族整体是个既尚武又守文的民族。比较崇尚勇力的时代,像周代,春秋战国与汉唐。但更多时候,尚武是一种礼仪和理想。周王举行巡守郊祀之礼,是为了实现“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理想。汉代承古之“讲武农隙,校猎因田”的制度,还在秋冬季节举行校猎的礼仪是为了让朝廷时时保持一种斗志来抵御外辱。 虽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毕竟是从很漫长很长远很间接的角度看的,解决当下的问题,还得靠社会精英阶层。在古代就是“士”。它开始专指“武士”,这是各级贵族禄养着专门替他们打仗的人,是战争的主力。周代最受教育的是武士。理想的武士不仅有技,并且能忠。把荣誉看得重过安全,把责任看得重过生命。后来士逐渐放弃武事而转向内心的修习,就是“文士”。由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这是一套传统的社会意识。他们在上以学术领导政治,在下以教育教化风俗。士人不受政府的摆布,以独立的姿态干预政治。这种社会从唐代开始,至宋代定型,一直延续到清代。往日领导政治的士阶层,日趋没落。往日士之精神,已渺不复见。近现代知识分子性质发生巨变,他们术业有专攻,从事于各个领域,而没有什么信念和政治意识,传统之士已经消亡。 张荫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玩“易”》, 借发挥《易经》的哲理,实际谈的是社会变迁与“革命”。短文直指《易经》的着眼处在生命,故曰:“生生之谓易。”近代流行的“革命”一词恰好是从《易经》的“革卦”里推演出来的。他认为,把“易”用在革命上,要懂得革命要新生,要懂得“生”不能急催。革命不等于寻死。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易一个旧的,岂是病夫易室,贵人易妻那样容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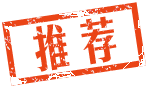
 /1
/1 